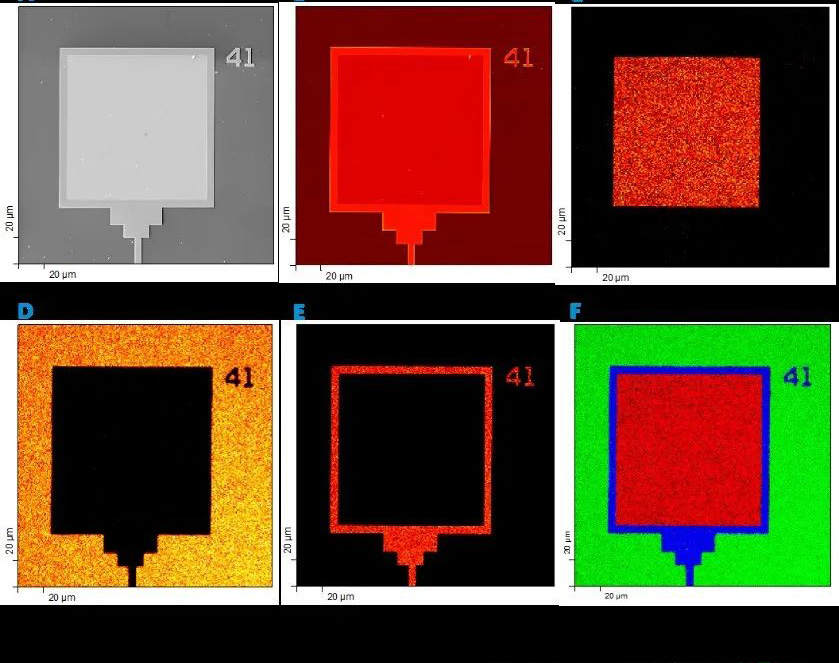
---案例1:郭某兰诉宾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治安处罚案件中“正当防卫”与“互殴”的区分(2024-12-3-001-022)
在当事人因琐事引发争执、导致双方动手的案件中,应当准确区分互殴和正当防卫的界限,避免简单机械地将任何形式的肢体冲突都认定为互殴。在区分时,需要全面考量案件的各种客观情节,包括事情的起因、对冲突的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采取了明显不相当的暴力等情节。一方当事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面对他人不合理怀疑和过激攻击,采取的反应手段在适度范围内,情节和损害后果等方面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原告郭某兰的丈夫、第三人黄某东及另外两名女子在奶茶店外喝奶茶打牌,其间,原告郭某兰进店买奶茶。因怀疑郭某兰进店时现场视频,黄某东要求原告交出手机并删除偷录的视频,原告否认偷录视频并拒绝交出手机。黄某东动手推搡原告头部,紧接着又朝原告的头部扇了一巴掌,同时也使原告手上拿着的奶茶飞溅出去。原告遂顺势将手中奶茶扔向第三人。紧接着黄某东抱住原告的身体往下压并且进行打击,原告则咬了黄某东的手指。经医院诊断,原告为创伤性牙齿脱落、左面部挫伤、左耳廓挫伤等身体伤害。黄某东为左手无名指软组织挫裂伤。原告报警,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公安局在调查后对原告及黄某东作出了相同的行政处罚,即拘留五日、罚款二百元。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其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2日作出(2023)桂0102行初10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郭某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郭某兰提出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宾阳县公安局自行撤销其对郭某兰的行政拘留处罚,上诉人郭某兰以其诉讼目的已经达到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撤回起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0日作出(2023)桂01行终248号行政裁定:一、准许上诉人郭某兰撤回上诉;二、准许上诉人郭某兰撤回起诉;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23)桂0102行初109号行政判决视为撤销。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告扔奶茶杯及咬第三人手指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准确区分两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判断原告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整个事件的起因来看,原告并无过错。本案的引发是第三人黄某东怀疑原告偷录了与其生活相关的视频遂要求原告交出手机,原告否认偷录并拒绝交出手机。本案中,公安机关并没有查明原告是否存在偷录行为这一事实,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偷录行为的情况下,黄某东要求原告交出手机并不合理,原告面对黄某东不合理的怀疑,拒绝提供其手机,是基于保护自身隐私的需要,并无过错。其次,从冲突的升级来看,第三人黄某东存在明显过错。
原告拒绝向黄某东提供其手机时处于克制状态,并未对黄某东采取主动攻击行为。相反,黄某东先动手推搡了原告的头部,紧接着又朝原告的头部扇了一巴掌,同时也使原告手上拿着的奶茶飞溅出去。黄某东先采取了过激的暴力行为,对原告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针对黄某东持续的威胁和攻击,原告才实施了扔奶茶的行为。紧接着黄某东抱住原告的身体往下压,原告才实施了咬对方指的行为。从上述过程来看,黄某东存在明显过错,其引发了此次冲突且造成了此次冲突的升级。
再次,原告行为属于面对当前紧急威胁的合理反应,且其反应的手段亦在适度的范围内。原告扔奶茶和咬手指的行为均是对黄某东突然的暴力行为的合理反抗,其目的是自卫,而非主动寻求对他人造成过度伤害。实际上,该行为也未导致对方遭受严重伤害,符合合理的防卫目标。
综上所述,第三人黄某东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怀疑原告存在偷录行为,要求原告交出手机予以检查遭拒后,对原告采取过激暴力行为。为使自己免受侵害,原告所采取的扔奶茶和咬手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非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宾阳县公安局在二审过程中自行撤销其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申请撤诉,予以准许。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23)桂0102行初109号行政判决(2023年10月12日);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桂01行终248号行政裁定(2024年1月30日)
---案例2:张某诉山东省桓台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正当防卫与互殴行为的区别(2025-12-3-001-002)
受害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的后果。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准确区分两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能仅看他人身体的伤害后果就将行为人的伤害行为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而应当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原告张某系某美食饭店经营者。刘某酒后到其饭店内就餐时遇到朋友,在与其朋友寒暄聊天期间,随手拿起朋友桌上一瓶瓶装啤酒用桌子边沿磕碰啤酒瓶盖。饭店经营者张某怕酒瓶盖子磕坏木制桌面,遂口头进行制止,引起刘某不满。刘某先实施摔酒瓶和辱骂等行为,后又推搡张某,双方发生争执直至厮打。其间,张某两次扔出空啤酒瓶进行还击。最终二人均摔倒在地,二人起身后,刘某头部受伤流血。经鉴定,刘某构成轻微伤。被告山东省桓台县公安局认定双方构成互殴,分别进行了处罚。以寻衅滋事为由,给予刘某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以殴打他人违法行为成立为由,给予张某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佰元的行政处罚(罚款已缴纳,拘留未执行)。张某不服对自己的行政处罚决定,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称其被刘某殴打后出于本能不自觉的从桌子上拿起啤酒瓶挥打,但是没有打到刘某,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故请求法院撤销被告桓台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3日作出(2021)鲁0321行初6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8日作出(2022)鲁03行终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不服,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2日作出(2022)鲁行申1233号行政裁定: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张某不服,申请检察监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日作出(2023)鲁行再6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3月28日作出的(2022)鲁03行终9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桓台县人民法院2021年11月13日作出的(2021)鲁0321行初64号行政判决;三、撤销桓台县公安局2021年1月15日作出的桓公(马)行罚决字[2021]3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用啤酒瓶殴打刘某致其头部受伤的事实是否清楚,张某反击行为的性质认定及是否应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一是关于张某反击行为的性质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1号)第2条、第9条规定,区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要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结合本案事实,可以综合考量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案发起因来看,刘某使用饭店的桌子开啤酒遭张某制止,而后刘某实施摔酒瓶、辱骂等行为,显属酒后惹是生非,情绪失控,明显过错在先。张某对冲突的发生没有预见和准备,利用随手拿到的身边物品进行还击,在冲突中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二)从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来看,本案从刘某突然猛推到二人被扶起,前后大约40秒时间,极短时间内,冲突并不是逐渐升级,而是整个过程持续相对激烈。刘某突然连续三次猛推和掐压张某,导致张某身体先是趔趄,后是坐倒,最后被压倒,整个身体处于下风状态,综合本案冲突全部过程,张某对冲突升级并无过错。(三)从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来看,刘某系年轻男性,身高约1.8米;张某系中年女性,身高约1.6米,体型偏瘦。刘某在身高、体重、年龄、性别等方面均比张某具有明显优势。当刘某猛推打张某时,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实施,立足当时处境,张某利用随手拿到的身边物品进行还击,且两次拿起的酒瓶均未碎裂即甩飞,击打明显不具有攻击力,并未采取明显不当的暴力,未超过必要限度。由此,张某的反击行为不能与刘某构成相互斗殴行为。综合考虑本案的起因、主客观因素、对象、限度等条件,张某的反击行为属于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桓台县公安局认定张某用啤酒瓶殴打刘某致其头部受伤的事实,证据不足,且不能准确区分正当防卫和相互斗殴的差别。
二是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问题。受害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的后果。《公安机关执行
有关问题的解释(二)》(公通字〔2007〕1号)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因此,公安机关在对当事人作出治安处罚时,不能仅看损害后果,还应当综合考虑案件的形成原因和损害发生过程。本案中,本次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刘某酒后寻衅滋事,率先发动攻击行为,再审申请人张某为了免受刘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随手拿起身边物品进行反击的行为,是为了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不予治安管理处罚。桓台县公安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给予张某行政处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第1款、第43条第1款;《公安机关执行
一审: 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21)鲁0321行初64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13日);二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3行终9号行政判决(2022年3月28日);其他审理程序: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行申1233号行政裁定(2022年10月12日);再审: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行再66号行政判决(2024年4月2日)
案例3:曾某龙诉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正当防卫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中的认定(2023-12-3-016-004)
【关键词】行政 行政处罚 行政复议 行政拘留 治安管理处罚 正当防卫 现实合理性
1.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违法行为人应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但受害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亦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的后果。此情形下受害人对违法行为人造成伤害的,公安机关在认定时,不能仅看他人身体的伤害后果就将行为人的伤害行为定性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行为而给予行政处罚,而应当根据治安案件所查明的事实,充分考虑伤害行为的起因和伤害发生的过程,综合判断该伤害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2.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在必要限度内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而不应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更不应因此给予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故受害人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伤害了违法行为人,其不是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且损害在必要限度内的,对受害人的伤害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而不应认定为治安违法行为而予以行政处罚。
在案外人徐某青家中,曾某龙与边某健发生争吵,后边某健用啤酒瓶将曾某龙头部打伤。后曾某龙和边某健二人夺曾某龙手中的手机,在夺手机过程中,曾某龙抓伤边某健面部、前胸、后背并咬边某健手部一下。后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接警后依法受理了案件,对各方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后经法医鉴定,曾某龙额骨骨折、右侧眶上壁骨折,伤情构成轻伤二级。边某健不要求进行伤情鉴定而未做伤情鉴定。后边某健因致曾某龙轻伤,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边某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对于曾某龙在本案中的行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临公行罚决字[20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XX年X月X日XX时许,在徐某青家中,曾某龙与同事边某健因说话恼了发生争吵,后边某健用啤酒瓶将曾某龙额头打伤。后双方夺曾某龙手中的手机,在夺手机过程中,曾某龙用手抓了边某健的面部、前胸、后背几下,曾某龙张嘴咬了边某健右手一下。边某健未做伤情鉴定,曾某龙伤情已构成轻伤二级(另案处理)。以上事实有曾某龙、边某健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现场照片、伤情照片等证据证实。”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综上认定曾某龙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之规定,决定给予曾某龙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曾某龙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2月7日作出临政复〔20XX〕XX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作出的临公行罚决字[20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曾某龙仍不服,认为边某健受伤不是其故意行为所致,是边某健阻止其报警抢夺手机过程中导致,其是正当防卫,故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庭审中,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明确表示:该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曾某龙和边某健二人争夺手机前为第一阶段,二人争夺手机为第二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即争夺手机前曾某龙和边某健二人是否存在相互殴打行为不能认定,但第二阶段即争夺手机过程中曾某龙和边某健都详细阐述了存在相互抓、咬对方的违法行为,存在相互殴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21)鲁0305行初73号行政判决:驳回曾某龙的诉讼请求。曾某龙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6日作出(2021)鲁03行终24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5行初7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临公行罚决字[20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三、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临政复〔20XX〕XX号行政复议决定。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违法行为人应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但受害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亦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的后果。此情形下受害人对违法行为人造成伤害的,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应当审查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受害人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伤害了违法行为人,只要不是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且损害在必要限度内,受害人的伤害行为即属于正当防卫,而非违法行为,其不应再因此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故公安机关在对治安案件进行认定时,不能仅看他人身体的伤害后果就将行为人的伤害行为定性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行为而给予行政处罚,而应当根据治安案件所查明的事实,充分考虑伤害行为的起因和伤害发生的过程,综合判断该伤害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还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根据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在临公行罚决字[20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也是本案中能够认定的事实),本案并不能认定且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在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中亦未认定第一阶段曾某龙和边某健互相殴打的事实,但能认定且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在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中亦已认定第一阶段曾某龙被边某健用啤酒瓶打伤额头。在此情况下,曾某龙系在之后的第二阶段即双方夺曾某龙手中手机的过程中对边某健造成的伤害。而曾某龙对边某健造成伤害的起因实际系边某健抢夺其手机。而在曾某龙已被边某健用啤酒瓶打伤头部后,曾某龙欲用手机报警是正当行为,并不属于事先挑拨或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的行为。且涉案手机系曾某龙个人合法财产,无论边某健是否出于阻止曾某龙报警的目的,在未经涉案手机物权人曾某龙的允许下,边某健均无法定或约定的抢夺曾某龙手机的权力,边某健在此情况下抢夺曾某龙的手机显然属于不法侵害行为。故曾某龙作为涉案手机的财产所有权人,其不让边某健夺走其手机而在边某健与其夺手机过程中将边某健致伤,明显属于为使其本人财产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范畴。
因此,综合本案案情,根据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和本案认定的事实,曾某龙在其与边某健双方夺自己手中手机的过程中对边某健造成伤害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受到治安管理的行政处罚。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曾某龙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系法律定性和适用法律错误,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在复议决定中认定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曾某龙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系适用依法正确和处罚适当,显属错误,其决定维持临公行罚决字[20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亦属错误,依法应当一并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6条、第9条
一审: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5行初73号行政判决(2021年7月29日);二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3行终243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26日)
---正当防卫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运用与认定-鲁法案例【2025】179(来源:山东高法)
2023年10月18日上午,张某某、王某某(夫妻关系)通过手机上的监控录像发现其饲养于楼区门头房前的4只狗崽于10月17日晚被邻居赵某某6岁儿子抱走,双方通过微信沟通未果。2023年10月18日20时许,在该门头房前,张某某与酒后至此的赵某某父子相遇,张某某因饲养的小狗丢失问题,询问赵某某之子,赵某某以张某某的行为吓着孩子为由先动手拍打赵某某面部,后两人发生争执继而互相殴打。经鉴定,张某某左眼眶周肿胀、左眼上睑稍青紫,之损伤为轻微伤;赵某某右前额部多处小片状擦挫伤、红肿,之损伤为轻微伤。公安机关组织张某某、赵某某进行治安调解,双方未达成和解。
2023年10月20日,张某某之妻王某某到周村区北郊镇派出所报案。当日,该所将此案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案。公安机关履行调查取证、委托鉴定、审批等相关程序后,于2023年12月2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张某某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对赵某某给予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张某某不服该行政处罚,提起行政复议,后不服行政复议决定,遂向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实施治安处罚必须在违法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根据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作出相应的治安处罚决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公安机关认定的张某某殴打赵某某的违法事实是否成立;二是公安机关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处罚幅度是否适当。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该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违法行为人应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但受害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的后果。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执行
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关于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中,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该规定实际上是对正当防卫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运用,即受害人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伤害了违法行为人,只要不是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伤害,且伤害在必要限度内,受害人的伤害行为即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故公安机关在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罚时,不能仅看损害后果,还应当综合考虑案件的形成原因和损害发生的过程。本案中,张某某因饲养的小狗丢失问题询问赵某某幼子,赵某某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吓着其孩子,为此引发本案。张某某辩解其实施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虽然赵某某先动手实施了拍打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在张某某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赵某某仍继续侵害,而是双方发生争执后均未冷静处理,进而导致肢体冲突,张某某认可其用拳击打赵某某头部,张某某的行为超出了制止违法侵害的目的,不具有必要性及正当性,并非正当防卫,双方属于互相斗殴的行为。对于张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行政处罚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赵某某以吓着孩子为由先拍打张某某头部,才进而导致后续的肢体冲突相互打斗,赵某某在本次纠纷中过错程度重于张某某。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本次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责任、具体情境、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赵某某给予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从轻给予张某某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幅度并无不当,没有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综上,张某某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人采取的制止行为,正当防卫是公民对不法侵害及时进行自我救济的权利。我国民事、刑事领域都对正当防卫做了明确规定。
在治安执法领域,虽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但根据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执行
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该规定实际上是对正当防卫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运用,即受害人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伤害了违法行为人,只要不是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伤害,且伤害在必要限度内,受害人的伤害行为即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认定某个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要符合以下五个方面的构成要件,一是存在不法侵害。根据《正当防卫指导意见》第5条,不法侵害既包括侵害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害人身自由、公司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只要有不法侵害发生,就可以实施正当防卫。二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表现为不法侵害已经发生且尚未结束,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危险性。如果不法侵害行为尚未发生或已经结束,则不能进行假想防卫。三是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只有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才能达到制止、阻却不法侵害行为持续发生的目的,故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实施人实施,不能对与侵害无关的第三者。四是主观上具有防卫意图。因遭受不法侵害而进行防卫的人,必须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害而采取防卫行为。如果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伤害,然后以制止不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实施侵害,则不属于正当防卫。五是防卫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防卫行为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是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防卫的强度和损害结果与不法侵害行为的强度和损害结果基本相当。防卫与不法侵害相差悬殊明显过当,或者防卫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失,是防卫过当,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违法行为人应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本案中,张某某因饲养的小狗丢失问题询问赵某某幼子,赵某某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吓着其孩子,双方发生争执进而引发本案。张某某辩解其实施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虽然赵某某先动手实施了拍打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在张某某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赵某某仍继续侵害,而是双方发生争执后均未冷静处理,进而导致肢体冲突,张某某认可其用拳击打赵某某头部,张某某的行为超出了制止违法侵害的目的,不具有必要性及正当性,并非正当防卫,双方属于互相斗殴的行为。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准确区分二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要综合考虑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等客观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因琐事发生争执,行为人超出了制止违法侵害的目的,其行为不具有必要性及正当性,不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属于互相斗殴的行为,故应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根据过罚相当原则予以处罚。
---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处罚——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释义(摘自:尹少成主编《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讲义》)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处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
本条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概念,但从对“制止行为”的具体表述来看,与《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即都是实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差别主要在于,《刑法》第二十条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本条重在规定公民个人“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但显然,公民为了防止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制止行为,也同样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故根据当然解释,本条也同样应当扩大适用到所有“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的情形。
因此,行政处罚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行政处罚责任。通常认为,正当防卫是国家确认并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家法律确认的公民在公权力保护不能及时到达情况下的一种私力救济权,是公民与不法侵害人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正当手段。正当防卫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最后手段,或者“不得已”的最后私力救济方式和应急措施,正当防卫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实践中,适用正当防卫制度应当遵循鼓励和支持的价值立场,体现优先保护防卫人利益的新的政策导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作为当前正当防卫机制的重要价值观基础,不仅是纠正防卫过当认定误区的关键,更是彰显人性本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重新激活正当防卫机制的根本内因。这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而言,意味着防卫限度不是简单的“结果对比”,也不是简单的“形式匹配”,而必须考虑防卫人行使权利的优位性及其“自保”的特殊性。
有利于防卫人的权利优先立场是指:(1)设身处地地优先考量防卫人的正当利益,防卫行为通常是公民的本能应急反应,强求防卫人实施绝对精准、拿捏有度的防卫,刚好对不法侵害行为予以制止,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2)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以正对不正”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质属性,表现为“正义行为”对抗“不法侵害”,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与认定存在模糊与争议之际,应当倾向性地作出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包容防卫人在此情此景之下无法周全、谨慎地选择相应的防卫手段,从而作出符合法理和情理的判断。(3)不能预设“绝对理性人”的事后判断立场,防卫人基于人的本性很有可能在惊恐害怕、慌张无措的情况下实施防卫,而绝不可能对限度的拿捏具有冷静思考。
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上,通常情况下,既要求防卫行为可以对不法侵害起到制止作用,还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性质、激烈强度、造成损害等方面不至于过于悬殊。如果防卫行为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且手段性质、激烈程度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甚至小于,就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无论最后是否造成重大损害结果。如果防卫行为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本来采取较小强度的防卫行为就足以制止其面临的不法侵害却采取了强度特别大的防卫行为,就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因此,认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主要是根据防卫方式、强度、手段不适当等情形,包括防卫行为人攻击部位的不适当、防卫工具的不适当、因防卫方人数或体能优于侵害方的情形下实施防卫行为等情形。所谓“明显”,不是一般的超过,而是显著的超过。在一般人看来,往往是一目了然或基本没有争议的。这是对防卫人有利的限度规定。基于此,通过分析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双方的人数、力量对比、持有凶器等情况以及当时的危险状况等所有案件情况,进行全盘考虑判断,再综合决定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具有必要性、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对“明显”的判断,更应有利于防卫人。
“造成较大损害”是防卫过当在结果上的成立条件。“较大”的损害结果,不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且相适宜的程度,而是在防卫行为过当的前提下所呈现出的一种结果过当。只有在行为上过当和在结果上造成较大损害,且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最终认定为防卫过当行为。总体上,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认定是否“造成较大损害”,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侵害相比明显失衡,可以认定“造成较大损害”,但一般不包括造成被害人轻伤或财产方面的损失。另外,还应当防止唯结果论的做法,即在观念上认为只要出现死伤结果就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这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认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其规范解释的两个关键要素是行为限度与重大结果。对此,应当基于综合判断的立场,从防卫行为与结果层面进行实质的判断。一是判断防卫限度不能脱离防卫行为的具体情况。防卫人对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的认识、防卫人的防卫目的等都是需要考察的因素。在实施防卫行为时,不能实施超过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且被禁止的多余行为。在合理与适度的范围内,基于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立场等,应从防卫权的优位性出发,对防卫行为的必要性进行相对宽松的认定。二是防卫的后果是以防卫行为为前提的,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的整体性制衡。只要没有明显超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继续进行的限度,并造成不应或没有必要出现的重大损害,就不属于“造成较大损害”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讨论正当防卫限度时,对防卫行为与防卫结果是否都明显“不当”,需要同时考虑行为与结果及其内部关系。根据社会一般人的通常理解与可能反应,站在防卫人防卫当时的立场,遵循“行为一结果”的逻辑进路,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进行具体判断与实质判断。防卫措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结果造成重大损害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只存在其一情形的,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
《刑法》(2023年修正)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原标题:《治安行政处罚中正当防卫与互殴行为的区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汇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